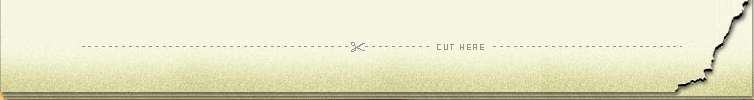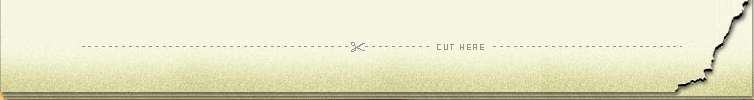半夜醒來,月光傾瀉如水。起身走到窗前,一顆明亮的星星掛在藏藍色的天邊,猶如一滴碩大的淚滴,晶瑩剔透的閃著冰冷的光。喜極了“光陰”這個詞,感覺像是塊顏色明亮的冰絲綢布。看著人心生燦爛,裹在身上,冰涼透骨,有著盛世的孤單與凜冽。光陰許是這世上最快的東西吧?不知不覺中,大把大把的青春已經呼啦啦的從身邊跑過,竟不容你有半點的拒絕與商討。
推開思念的門,奶奶圍著她的小碎花圍裙,從最柔軟的光陰裡走出。小時候,父母工作忙,我被寄養在奶奶家。奶奶是習慣了早起的。每個清晨,我從睡夢中醒來,賴在炕上,聽著她輕輕的拉著風匣,干柴塞進去,松枝發出 啪脆裂的聲音。後來會有水瓢觸碰到鐵桶邊緣清脆的作響,那是她做完早飯在澆花。她是愛花如命的老太太,門前栽了兩棵榕樹,睡蓮,月季,玫瑰,百合,君子蘭,還有很多我叫不上名字的花花草草,被她井然有序的安放在院子的每一個角落。每當夏日的傍晚,我最喜歡的事,便是趁她煮菜的空隙,赤腳爬上平房。白天裡被太陽烤的溫熱的石板,溫吞吞的親吻著腳底的每一寸肌膚。有風吹過時,帶著一陣陣甜糯的花香沁入心脾,干脆躺在石板上,瞇起眼睛看著西邊天空各種顏色火燒的雲變幻著形狀爭奇斗艷。找不到我,她便一邊解下圍裙一邊仰著頭喊著我的乳名。直到我竄到她面前,她佯裝生氣的高高抬起手,又輕輕的落在我的屁股上。四周漸漸暗下去的光映著她滿臉的慈愛,我吐著舌頭沖她扮鬼臉,她便撲哧一下笑出了聲。
西面的小屋裡有一個藏紅色的箱子,是她陪嫁的嫁妝。裡面裝滿了紅的綠的粉藍的各種花色的綢布。每逢過節的時候,她便從裡面找出幾塊滿意的料子,如變魔術般的做成漂亮的小褂,穿在我身上。她總是一邊看著我一邊笑著說︰“人靠衣裝馬靠鞍,小丫頭打扮起來就是俊﹗”然而我最惦記的,是箱子裡的那個褐色的樟木盒子,小小的,竟然被她上了鎖。她從來沒有打開過,也從不允許我動它。我曾試圖用小木棍撬開它,可每一次都沒有成功就被她捉到。它就像一只神祕的寶盒,散發著詭異的光,我一直都在想像,裡面是一個金元寶?一枚古老的玉?還是?
後來父母把我接進了城裡,我忙著升學,工作,漸漸的回老家的時間少了。每當得知我要回家的日子,她就早早坐在門前的榕樹下,抻長了脖子等我。看到我的身影在巷口出現,她就用最快的速度進屋,拿出她熱了又熱的飯菜,笑瞇瞇的看著我大快朵頤。知道我戀愛了,她突然變得比誰都緊張,遇到家裡的親戚就問︰“怎么樣?你們覺得怎么樣?”後來問的大家都煩了,見了面就對她說︰“挺好的,挺好的哈﹗”她才瞇著眼,點點頭開心的笑笑。最後一次見她,我離預產期還有一個月。她走路還是硬朗朗的,只是血壓有點高的讓人擔心。她摸摸我的肚子,又拽過我愛人的手,很神祕的低聲說︰“我留了個寶貝給你閨女”又指指我說︰“她生下來的時候,小小的,我捧在手心裡,就這么小﹗”她有點誇張的用兩只手比劃著,引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。
沒過有人告訴我,生命的輪回竟可以這般的殘酷。給孩子辦盈月酒席之前,我一直都沒有見過她。大家都說她在忙,統一的口徑,同樣的理由,我起不了半點的疑心。那晚,送走所有的賓客,母親紅著眼睛告訴我,她走了。就在我住院待產的第一個周,是因為急性腦出血,做過兩次開顱手術。清醒的時候她交代所有的人,不管發生什麼事情,都要保證我坐好月子。她走的時候轉著頭到處看,母親趴在她耳邊說︰"囡囡挺好的,挺好的哈﹗”她才笑笑,閉上了眼睛。一個沉甸甸的小布包放在我的手裡,打開包裹,是一件紅色的小肚兜,柔柔涼涼的緞子,上面是粉色絲線繡製的一朵睡蓮。一個沒戴鎖的褐色的樟木盒子,裡面靜靜的躺著一把銀質的小項鎖。我知道,睡蓮是她最愛的花兒,她的名字裡有 “蓮”字。我知道,小項鎖是祖上從宮裡傳下來的東西,她一直當寶貝似的給我留著。我知道,她要我過的好。我咬著牙強忍著,把肚兜貼著胸口緊緊的抱著,那一夜,淚眼模糊的我沒有哭出聲,我怕她聽到,她會擔心。
月涼了。凌晨時分的天空,有一種夾雜著灰紫的淡藍色。窗外傳來露水和植物的芬芳,愛人翻了個身,又沉沉的睡去了。孩子做了個夢吧?囈語著,兀自的咯咯笑了幾聲。我用您愛的針腳穿起思念的線,在光陰這塊冰涼的絲綢上繡一朵朵溫馨的花,歲月靜好而純真,您,看的到的,我知道﹗
|